【www.chinawenwang.com--歇后语】
王婆卖瓜----烂杏别充好桃《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上黄杲炘先生发表了一篇大文,题目是《英诗汉译:发展中的专业》,内容是为百余年来的英诗汉译做总结。不过文章开始是对杨振宁的批判然后才是通过英国诗人Thomas Gray 的名篇Elegy 第一小节的不同译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英诗汉译指出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我想对这两方面也谈一点看法。首先是杨振宁的挨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是,他不该说“连最美的诗句也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物理学的美”;第二点是,黄先生作为诗歌译者感到奇怪,为什么杨教授在著名高校引述这首诗不用原作却用译文;第三点是所引译文既不符合原作意义也不美,不该用它和物理学相比。
我认为关于“美”,往往既有大家公认的客观标准又有每个人不同的主观认识,杨先生可以认为物理学最美,黄先生可以认为自己译的诗最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大家各人都有自由。关于第二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倒对黄先生有点奇怪,为什么杨先生在中国为中国著名高校学生讲话的时候,引用资料就不该引用译文而一定要引用外文呢?至于第三点,黄先生认为杨先生所引译文不好,只有黄先生所给的两种译文才是最好。我忽然想起哈姆雷特剧中的一句台词,那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现在我们就做一番具体考查。
下面我把把蒲柏为牛顿所写挽词的原文、杨先生所引译文,和黄先生译文一并列出。(保留了黄先生用符号〡标出原文的音步和他自己译文的顿)。
蒲柏(Pope)的原文;
Nature ▏ and Na ▏ture’s laws ▏ lay hid ▏ in night:
God said , ▏ Let New ▏ton be! ▏ and all ▏was light.
杨先生所引译文: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
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真光明。
黄先生所译的两种译文:
译文1:
自然 ▏和自然 ▏法则, ▏在黑夜中 ▏隐藏。
上帝说 ▏要有 ▏牛顿! ▏于是 ▏就有了光。
译文2:
自然、 ▏自然 ▏法则 ▏在黑夜中 ▏隐藏。
神说 ▏要有 ▏牛顿! ▏随即 ▏都有了光。
黄先生首先阐明了蒲柏对句的主旨是“以最经济的词语对牛顿作了最高的评价:自然和自然规律原先不为人知,有了牛顿,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功绩之大几乎可以和上帝初开混沌相比。”然后黄先生指出了蒲柏对句的四点美,第一是押韵,第二是抑扬格五音步,第三是头韵,第四是套用圣经句式: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汉译为: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或把God 译为神)。因此这对句就有庄严感和神圣感,甚至让人有敬畏感。当然黄先生认为自己的译文是符合原意并且传达了四个美点的。
现在,也让我们来体会体会黄先生译文的美吧!蒲柏对句的节奏美主要表现在抑扬格五音步,黄先生以顿代步,那么请问抑扬格哪里去了?五音步哪里去了?抑扬格是两个音节,前轻后重,五音步是十个音节。黄先生译文一,十三个音节,第一行的第二顿是三个音节,第四顿是四个音节,第二行的第一顿是三个音节,第五顿是四个音节。这与抑扬格五音步根本不贴边儿。译文二,有十二个音节,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说不同语言节奏美构成的元素是有差别的。就算黄先生用汉语构成了抑扬格五音步也未必就是具有节奏美的汉语。因为,英语是重音语言,主要靠轻重律构成节奏;而汉语是音调语言,构成节奏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不禁使我想起东施效颦的故事。同样的动作在西施那里是美丽的,在东施那里却没有效果。如果把杨玉环的霓裳穿到赵飞燕身上大概是曲线难显,用赵飞燕的舞衣裹紧太真贵妃的玉体也许会挣破罗绮泄露春光吧!一个正常人应该不会认为从一位美人身上取一副耳环拿一个发夹给另一位美人佩上这就完成了化妆任务。那样一位毫不考虑特点的化妆师也就太不值钱了。说到什么神圣感,我觉得作为一个阅读译诗的普通中国人(灵魂里浸透了西方文化的除外)可能不会有那种体会。另外,圣经里面的“there was light .”是 there be 句型,这里 “light” 是名词,所以翻译为“有了光”;而蒲柏对句里的“all was light.” 是主系表结构,这里的“light”是形容词,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切都清晰(或者明亮、光明)”,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大白于天下”,套用圣经译为“有了光”,既背离了原文,对圣经也是一种不公平吧!就这一点而言,杨先生所引译文倒比黄先生的译文还更准确。不过,这本是中学生应该理解的最基本的语法问题,似乎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何况形式应该是为内容服务的,译作“有了光”押了脚韵,却背离了内容,岂不是得不偿失。再说,译作是给中国人看的,至少应该让普通中国人感到一点美吧!只有黄先生自己能分析出美,感觉到美还是不够吧!如果从汉语的角度来分析,黄先生的两种译文并不符合汉语对句的要求,汉语对句最大的特点是对称,字数、词语、声律都要相对,而黄译除字数相等,其它无从谈起,根本不能体现对句的美。
那么蒲柏对句还可以怎样翻译呢?我认为以下的译文都比黄译为好。
译文3:
自然及其法则暗中隐藏,
神说要有牛顿一切见光。
译文4:
自然法则隐于暗夜迷雾,
天生牛顿揭示运行规律。
我们还可以根据原文所蕴含的内容调整词序得出以下的译文,
译文5:
上帝说,鸿蒙世界待启动;
牛顿生,自然规律全揭开。
译文6:
上帝发话,混沌世界须启动;
牛顿降生,自然规律全运行。
译文7:
上天忧虑,宇宙谜团藏暗夜;
牛顿降生,自然规律见光明。
中国读者对以上译文应该能够易于接受,因为都较好接近于对句的形式,符合于中国诗上下联的规律,能够体现出韵律美。内容上也完全表达了黄先生所阐明的主旨,即:“自然和自然规律原先不为人知,有了牛顿,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功绩之大几乎可以同上帝初开混沌相比。”但这并非刻意遵循抑扬格五音步而来,实乃遵循了汉语的音顿律、声韵律和平仄律的要求。由此可见,黄先生硬搬英诗音步的做法,根本不能体现原诗之美。
关于蒲柏为牛顿所写的挽词就谈这些,下面再谈谈关于Thomas Gray 名篇Elegy 第一小节的问题。现录原诗于下:
The curfew tolls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黄先生文中举出了六种译文进行了比较和评述,并确定出认为是从内容到形式最贴近原诗的译文,也就是黄先生自己的译文,现转录于下:
晚钟敲起,为逝去的白昼送终;
牛群哞哞,在牧场上迤逦慢走;
耕夫回家,疲惫的脚步缓又重;
这个世界,就留给了我和昏幽。(黄:79)
首先,我认为黄先生虽然参考了各家译文,但却未能读懂原诗。因为原诗表现的是一幅动态的画面,有声有景,在时空变化中渲染了人的情感。而黄译的第一句,就脱离了原诗,破坏了整个小节的有机构成,使之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罗列。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的问题出在对“parting”的理解上,我们看“parting day”,应该是“正在离去的白昼”,或“即将逝去的一天”,如“parting request” 是临别的请求,“parting kiss ”是临别之吻(吻别)。所以原诗反映的是过程,是“白昼”将去未去,正在离去,就是黄昏时分,也就是老百姓口语里的傍晚。这样才留有展现后面场景的时段。译成“晚钟敲起,为逝去的白昼送终”则展现的是结果,意味着“白昼已经过去”。因为昼和夜是相对的,昼指的就是从天亮到天黑的一段时间,黄昏包括在昼的时间段以内。如果 “白昼已经过去”,那就是黑夜已经降临,在一片昏黑里什么也看不见,根本不能存在后面的场景。这样就对原诗的结构造成了破坏。因为原诗所展现的是过程,所以在这个时段里可以看到牧场上牛群的行进和归途上耕人的脚步,最后再归结到暗夜的降临。另外,顺便说一句,“昏幽”一词似乎有生造的味道。
其次,再说说格律的问题。当然格律也是重要的,译格律诗不能忽略节奏美。但是当内容已经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节奏美自然也要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可是,不同的语言构成节奏美的元素是不同的。英语是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语言,每个音步包含一个重音,根据该重音与轻音的不同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音格。英语格律诗的格律就是由音格、音步和每个诗行最后一个音步的韵式决定的。按抑扬格、5音步、abab的韵式来诵读这小节英文原诗,确实能够感到其韵律之美。但汉语是以音节计时的声调语言,主要以音顿律构成音步节奏周期,它的节奏美是根据音顿律、声韵律和平仄律的周期性往复构成的。先不说把黄译每行划作5个停顿是否合适,就按抑扬格来说,能把译诗中每个“停顿”里出现的汉语双音节词都标作前轻后重吗?何况“为逝去的”和“在牧场上”等最后一个字都是轻声。如果把每个停顿都看作抑扬格,试试看,这样读出来还像中国人说的汉语吗?如果不按抑扬格去诵读,那么,刻意模仿原诗的音步还有什么意义?要知道一首诗的音格、音步和韵式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体现其美学特征的。黄先生把所译之诗行划作五个音步,以为这样就体现了原诗的节奏美,其实是南辕北辙,根本达不到目的。
现在我们抛开抑扬格5音步,就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一首中国诗,我曾反复多遍诵读黄先生的译诗,但却读不出诗所应该具有的韵律美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部分组成,这就决定了音顿律(或长短律)、平仄律、声韵律为汉语节奏的主旋律。而平仄律也就是平声音节和仄声音节交替是汉语特有的,也是汉诗特有的。从译诗的第一句看,如果按照汉语音顿律,把它按音节切分成(2+2)+(1+3)+(2+2)的音步形式,那么虽然在“晚钟敲起”和“白昼送终”里有一个音步层双声,但是这一个音顿节奏的周期性往复并未能产生很好的音乐效果,因为同音字必须处在节奏周期相应的位置上方可出声韵律节奏周期;若同音错位,则读来拗口。而 “钟”和“终”就犯了同音同调隔字相重而又错位的毛病。这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所指出的“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
其第二句“牛群哞哞,在牧场上迤逦慢走。”切分成(2+2)+(1+3)+(2+2)的形式,与第一句形成音顿节奏周期性往复,还有一个音步层叠音“哞哞”和一个音步层叠韵“迤逦”,可惜受第一句声病的影响,未能形成好的韵律感。这也可能与句子开头一连4个平声字接着一连8个仄声字,两者都过分密集,缺乏错综有一定关系。
第三句应切分成(2+2)+(3+2)+(1+2)的形式,句子内根本没有节奏层周期性往复,只有结尾的“重”字和第一句结尾的“终”字押了一个不同调的韵,而在汉语诗歌里,除句句押韵外,从不理会单数句子的押韵。
第四句应切分成(2+2)+1+(3+1)+(1+2),同样句子内没有节奏层周期性往复,和第三句也属于不同结构。只有结尾的“幽”字和第二句结尾的“走”字押的不同调的韵。
虽然从整体上是(abab)的韵式,但第一、二句和第三、四句构造不同,也形不成排比,所以没有汉语诗歌的韵律美。
诗歌翻译的任务应该就是传达原诗的美,这包括内容意境的美和形式即节奏韵律的美,既然内容意境是用汉语表达的,那么形式也只能用汉语的节奏韵律来表达。抛开汉语的特点,照搬原语的节奏韵律,当然无法达到美的要求。
汉语诗歌一般采取(aaba)或(abcb)的韵式,运用音顿律、平仄律、和声韵律的套叠产生韵律美。我个人认为这节小诗可以试译如下:
敲起暮钟,送别迅将消逝的一天,
群牛吼叫,纡越牧草离离的荒原,
耕人回舍,迈出疲惫沉沉之脚步,
天色渐暝,惟留孤独小我与黑暗。
也可译为:
晚钟敲起,送别即将逝去的白昼,
牛群哞哞,纡越牧草离离的荒野,
耕人回舍,迈动蹒跚沉沉之脚步,
天色渐暝,惟留暗夜寂寂与小我。
黄先生是专业诗歌译家,对于诗歌和翻译,我都很业余,贻笑大方,在所难免,不自量力,愿得指正。下面也就英诗汉译的发展与专业化谈一点看法。
黄先生推崇的译文“要求诗行字数、顿数分别与原作行数、音节数、音步数相应和相等(用长音或双声、叠韵反应原作中的长元音和头韵则是另一回事)”。又说,“译者在实践中逐步发现了汉语汉字反映原作内容与格律的潜力,使反映成为可能。”。黄先生还说,“在逐渐‘逼近’原作的过程中,拓展‘可译’或可以设法反映的领域,把原作中一些较细微的差别也反映出来。”现在既然已经逼近到行、音格、音步、音节数目的相等,以及长元音和头韵,还要拓展到更细微的层次,那也许就只能是音素了。
我认为“逼近”原作,应该是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吃透原作的基础上,逼近原作的美,这当然包括内容也就是意境和韵律两个方面的美,但这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在表达上无疑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对美的认知上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不论对意境美还是韵律美,都只能是有所取舍,有所补偿。如果强行把一种语言的韵律原封不动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未必能符合美的要求,事实上这也根本不可能。至少在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这种移植是无法操作、无法实现的。英诗汉译就应该具有汉诗的美,在意境美上要符合汉语的要求,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在韵律美上当然也应该符合汉语的要求,也可能有不同的表达,而不应该是照搬原诗的韵律。更不能是要求从音步、音节甚至到音素的相等。
黄先生对“诗人译诗”颇有微词,认为“或许较有诗意”,但是还应该“专业化”。难道“诗意”和“专业化”是对立的吗?黄先生所指的专业化是什么意思?是把英语里的音格、音步、音节、甚至音素都原封不动移植到汉语里来吗?黄先生还说:“如果不反映格律,那么即使每首诗都是好诗,整体上却是杂乱无章的,蕴藏于格律中的美和信息将全部丧失。”我认为既然是好诗就不可能没有格律,就会有蕴藏于格律中的美和信息,也不会是杂乱无章的,没有必要因为它不反映英语的格律就加上“杂乱无章”的罪名。
黄先生在文中自己定位是发展中的少数派,我却不敢苟同。黄先生有大量的译作,在《中国翻译》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拥有不少读者,曾任《译文》主编;还有屠岸先生有着极为丰富的诗歌译作,还曾任《人民文学》的主编。两位都是力挺要按原诗节奏译诗的。而《译文》和《人民文学》又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刊物,因之拥有很多的追随者是非常自然的。《中国翻译》作为国内权威的翻译理论刊物,也多是刊登对按原诗节奏翻译诗歌的赞扬文章,影响所及,文学刊物的编辑大多数也都是贵派的追随者。差不多主张翻译要充分注意汉语特点的人,一出手就会被打入不懂英语的林纾之流。像杨振宁先生只不过在报告中引用了几句未按英诗节奏翻译的小诗就遭到黄先生的痛批,何况其他人。现在除了钱钟书先生曾经对我国翻译现状发过几句感慨以外,似乎汉语英语化已经成为当前一股异常汹涌的潮流。虽然如此,令人遗憾的是,英诗名作,汉译出来之后,没有几篇能够得到广泛传诵或流传。这或许和太缺乏汉语诗歌的韵味不无关系,我们固然不应该抱残守缺拒绝吸纳新事物,可也不应该数典忘祖,把自己诗歌的特点完全泯灭啊。我认为英诗汉译的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努力发掘汉语韵律美的潜力,以逼近原诗的韵律美,而不是机械地照般英诗的韵律,而且要达到韵式、音格、音步、音节,甚至音素数目的全等。在这里我不知道:黄先生究竟是吹响了英诗汉译胜利进军的号角,还是敲响了英诗汉译迈入末路的丧钟;所指示的是一条阳关大道,还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我也看到一些英译的汉诗,多是用的英诗的格律,黄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资深译家,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也把汉诗的韵律移植到西方,让汉语的平仄也在英语里占一席之地,为宏扬中国文化做一点努力?我们的语言文字曾经创造出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的唐诗宋词能以流畅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辉煌于世界文学之林。我真的不希望通过英诗汉译把汉语的特点抹掉,使之逐步成为西方语言的臣仆。说几句可能有点离题的话,我记得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在被占领的沦陷区,在汉奸群里,流行过日语化了的汉语,什么“大大的好”、“死啦死啦的有”,那是一种极其令人痛心的现象。现在改革开放,我们应该也必须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但同时也不该忽视清除一切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强式文明固然使我们受益,对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侵扰和破坏,也在一步步加深,同样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那它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最终将不免趋于消亡。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决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在英诗汉译中已长期存在的“汉语英语化”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危险的倾向。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井蛙陋见,愿就正于方家。
更多相关内容:文档为doc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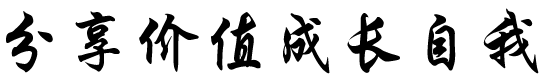




 2023-06-13
2023-06-13 






